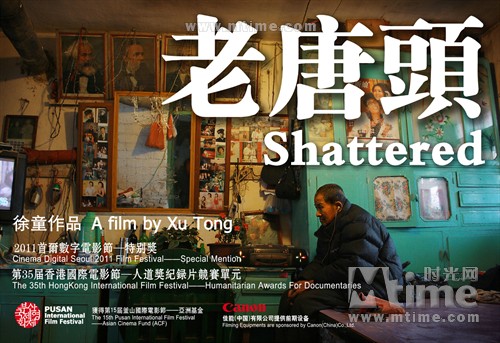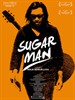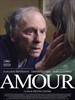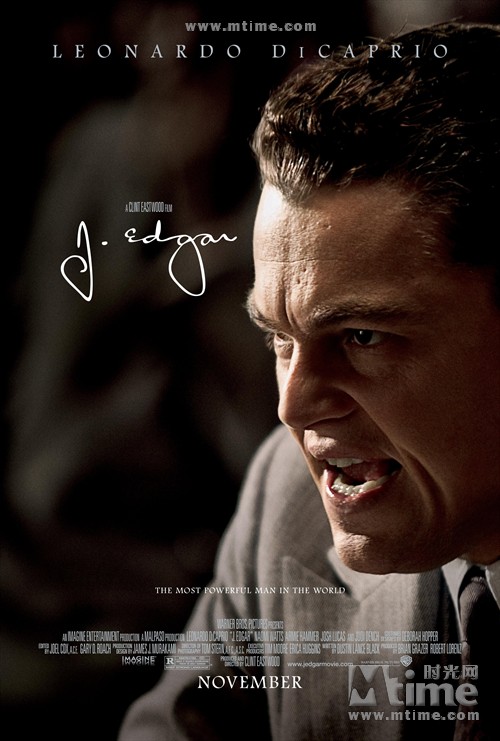妻子、情人、老伴:伯格曼的电视电影
伯格曼并不是一位只会拍电影的导演,除了电影之外,他还是一个戏剧大师,还是一个作家。相比较于电影,伯格曼更喜欢戏剧和写作。伯格曼自己曾经说:“戏剧像个忠实的妻子,而电影则是一场巨大的冒险,是一个既昂贵而又挑剔的情人——你崇拜两人,每一个都以它特有的方式。”1966年,伯格曼辞去了他任职了27年的瑞典皇家戏剧院院长的职务,而1983年,在把那部叫做《芬妮与亚历山大》的电视剧集剪辑成辉煌的电影之后,伯格曼则宣布息影,不再返回电影制作领域。很多人当时认为伯格曼会就此退休、卸甲归田。但是他们错了。在狭窄的缝隙之间,伯格曼寻找到了电视电影这个载体,并且一如既往地用属于他的镜头语言、人物和故事,表述着自己。如果戏剧是伯格曼“忠贞的妻子”,电影是伯格曼“高贵的情妇”的话,那么电视电影,则是伯格曼在晚年为自己找到的一位最可以放松和托付的老伴。
关于伯格曼所拍摄的电视电影的数量众说纷纭,不一而足。有资料表示是20余部,也有资料表示说不超过10部。如果按照严格的由电视台投资、只在电视台播放,没有大规模公映的标准来看,伯格曼所拍摄的电视电影除了下面详细叙述的五部之外,还有一部名为《小丑现身时》的讲述导演“发明”电影的影片。只不过,这部电视电影,在伯格曼的众多杰作中,缺乏相应的水准和内涵,所以,甚至在伯格曼自己的表述中,它都是缺席的。在这些伯格曼亲自导演的电视电影之外,他还为两部电视电影做了编剧,这两部影片分别是《善意的背叛》和他的御用女演员丽芙·乌尔曼导演的《私人谈话》——应该说,这六部电影(含一部纪录片)和两部编剧作品,是伯格曼留在电视荧幕上的全部遗产。
大师拍电视电影,我们该如何来评价?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限于载体维度和受众的原因,电视电影没有办法承担太多情感和内涵;限于资金和拍摄周期,电视电影不会有太大的场面和太多的场景。所以,我们在伯格曼所拍摄的这些电视电影中,看到的全部是对话——以及对话所构筑起来的世界。这些电视电影的故事,大多是短平快发展的,要么是审讯、要么是前妻探访前夫、要么是导演和女演员的“交流”、要么是对一出歌剧的记录——简而言之,伯格曼在自己的电视电影里,继承并发展了他的晚期的银幕特色:那种对家庭、对人性、对关系和对梦境的表达。
站在这个角度上,伯格曼手下的电视电影,是他电影生涯的一个延展和延续,也是他对电影这种艺术形式的探索。毕竟,在他的电视电影的作品序列中,我们看到了很多实验性的和戏剧相关的内容。比如分幕、比如只用对话来构筑整个作品,以及那些对梦境的犀利表达。在电影领域,早期的伯格曼在说性和婚姻;中期的伯格曼在说宗教斗争;中晚期的伯格曼则在玩精神分析;到了晚期,伯格曼在研究家庭。而在电视电影方面,伯格曼在剖析自己。所以,我们能认为《排演之后》的老导演就是伯格曼本人,《萨拉邦德》里的老鳏夫就是伯格曼本人,甚至是《仪式》里的那个突发心脏病死掉的法官,也是伯格曼自己。
用这些作品,伯格曼为自己的艺术生涯划上了一个句点,他也为自己的作品所表达出来的“生命曲线”添上了最后一笔。如果说,伯格曼的人物,具有单一心灵或者是叙事者的多个层面的话,那么,这些电视电影中的人物,则无疑是最贴近他内心真相的——因为卸去了大师的光环、没有了制片商的压力,伯格曼离自己的灵魂更近了……
《仪式》:摄影机与四个演员的运动
拍摄《仪式》的想法来自一个忙里偷闲的点子,那个时候伯格曼正在拍摄著名的《羞耻》。《羞耻》一片几乎全是外景戏,但是伯格曼和剧组还是搭建了一个可以拍摄内景戏的摄影棚,以便在天气不佳的时候,可以在这里再拍摄一部别的什么电影。于是,伯格曼就为了这个摄影棚,撰写了《仪式》的剧本。也正是因为如此,伯格曼才把《仪式》这部电影称为“摄影机与四个演员的运动”。只不过,和《羞耻》同期拍摄《仪式》的愿望没有达成,在《羞耻》完成之后,伯格曼找来了几位演员,用了一周时间排练,用了9天时间拍摄出来了这部就有极简主义倾向的影片。
看过《仪式》的人,或许会对影片最后一幕里的“现场演出”感到好奇,其实,这并不是伯格曼的原创,而是他的一个借用。在古希腊的时候,剧场表演常常会和宗教仪式联系在一起。观众们会在日出之前到达仪典的现场,带着面具的祭司,则会在黎明的时候出现。之后,当太阳升起并照射到舞台中央的时候,人们能看到在那里有一个小小的祭台,祭台上会有一个大型的器皿,里面装着的是祭祀动物的血。与此同时,一个带着金色面具,象征着神祇的祭司会躲在其他祭司的背后。当太阳升得更高的时候,两名祭司会把盛着血液的祭器举起,以便让观众看到金色面具在血液中的倒影。随后,群鼓齐鸣、牧笛狂响,祭司们会齐声高唱祭曲,主祭司在这个时候才会喝下祭器中的血液。这就是最后一个场景的由来。而这个奉举圣体的仪式,也成为了整部影片的关键点。
在这个仪式举办之前,法官一直在审问这三位演员的相关情况。可是当这些人带上了面具,便顿时变成了神灵。所以,法官会在“圣迹显现”的当下求饶。他恳求这三位艺术家把自己视作凡人。可是,这时却为时已晚,他犯下的是强奸罪,即将被问斩——可是,当刽子手的刀子还没有落下的时候,法官就已经先走一步了,他因为心脏病突发而离开了我们。
伯格曼在对这部影片的设计上,是颇具匠心的。在人物的安排上,他分别把一种人的三个侧面分别安排在了三个角色身上。在费舍尔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没有责任感、好色、情感不稳定、反复无常的性格;而在温克曼的身上,我们则看到了一种纪律性、遵从社会价值规范的典范。最后,在那个最复杂的女性角色蒂亚的身上,我们看到了是一种对自我性格的直接描述:这个角色岁数不明、面貌糊涂,敏感、没有建设能力、也没有摧毁能力,像是初生的婴儿,又像是神秘的外星来客。在伯格曼的其他电影中,蒂亚有着不同的“分身”。在《犹在镜中》里,她是和蜘蛛说话的卡琳;在《呼喊与细语》中,她是受制于的生与死以及自己情感的安妮;在《假面》里,她是处在性格转换之间的安曼和曼妲……站在这个角度上,《仪式》并不是一部简单的电视电影,而是一部可以放在伯格曼创作序列中被讨论的影片,除了舞台剧的形式感和伯格曼式的人物之外,这部影片还在幽闭空间的情绪积累上做到了极致——所以,著名的T·曼斯将这部在电视上放的电影称为“伯格曼的杰作”,也就不足为奇了。
《法罗岛档案》:被掩盖的布景
法罗岛是瑞典的一个旅游地点——但是仅限于夏季。法罗岛位于瑞典大陆东南格兰特岛以北,是一个在波罗的海上的小岛屿,人口少于600。虽然在夏季是热门的旅游地点,但是在其他三季之中,法罗岛上的生活还是乏善可陈的。没有娱乐设施、没有夜生活、一些地方甚至还没有电,也没有银行、邮局、医院和警察局,所以很多年轻人都无法在这里待下去,从而选择了走向斯德哥尔摩、基律纳这样的大城市。后来,这种瑞典青年人“北漂”的情节也被伯格曼放在了《法罗岛档案》一片中。
《法罗岛档案》一共有两部,第一部是拍摄于1969年的《法罗岛档案》,而另一部则是1979年版的《法罗岛档案》。伯格曼是在1960年发现的这个小岛,他对这个岛屿上的一切事情感到着迷。那个时候,正是《犹在镜中》的剪辑阶段。1966年定居于此之后,伯格曼在这个岛上拍摄了自己的最后几部作品。岛上的风土人情、生活习俗、风光景色、教堂、岩石、飞鸟、荒地、人群、坟墓、石碑,都成为了伯格曼后期电影中的组成部分。在1971年的《接触》一片中,伯格曼就在片中使用了一块他在法罗岛上发现的雕刻有古老文字的石碑。在镜头不断的逼视下,天空、陆地和海洋之间的空无一物成为了打开心灵的钥匙,而宗教感也就此产生。
1969年版的《法罗岛档案》是一部意外得来的电影。当时,伯格曼正准备和自己御用的摄影师斯文·尼克斯维特一起拍摄一部关于绵羊养殖的科教片。为此,他走访了法罗岛的大量家庭,他发现,岛上的居民依然生活在十分恶劣的条件下,他觉得资本主义的光芒还没有惠及于此,于是便萌生了拍摄纪录片的想法。影片用16mm的黑白胶片拍摄,拥有大量的采访。伯格曼很高兴于人们的声音让世人听到,虽然有上百万人在电视上看到了这部电影,但是外国媒体对影片的评价却并不算高。而十年后,更加理解小岛生活的伯格曼又重新拍摄了一部《法罗岛档案》。
因为税务问题,伯格曼曾经有一段算是不堪回首的流亡阶段。1976年的流亡期间,伯格曼心烦意乱,重新回到了法罗岛,几乎就在同一时间,他决定再拍摄一部关于这里的纪录片。在新版的《法罗岛档案》中,伯格曼把镜头对准了小岛上的普通人,记录了他们的生活;并且再次把十年前的一些对孩子们采访的镜头拿出,把十年之前和十年之后的人们做了对比。这是一部典型的拥有电视报道风格的纪录片,一切都不是偶然、没有遗漏也没有偏颇。所有的内容都是拥有热情的。那种“被掩盖的布景”,展示出的是一种神迹、一种热爱、一种人文、地理、叙述、历史和政治、经济、道德相互掩映的美好概念。
法罗岛,按照瑞典语的解释,说的是“旅游者的岛屿”,意指旅游者歇脚的地方。但是,在伯格曼的叙事中,这种“临时的栖息场所”变成了某种意义上的精神家园。其实,这个岛屿,真的是另一个电影大师的临时的歇脚地和精神家园。1986年,来到海外的安德烈·塔尔可夫斯基在伯格曼的资助和协助下,用全套伯格曼的班底,在法罗岛上完成了自己最后一部影片《牺牲》的拍摄。

《排练之后》:耳背的导演
《排练之后》是一部非常有趣的影片,伯格曼按照电视剧的拍摄手法拍摄了一部电影,其题材却是关于剧院的。整部影片一共只有三个角色:老年的导演亨利克·富勒戈、年轻的演员安娜和安娜的母亲蕾柯尔。影片一开始,亨利克·富勒戈在工作台边昏昏欲睡,突然安娜来访,她是要在剧院中找一只丢失的手镯。其实,丢失手镯只是借口,她是专程来和导演说话的。安娜的父母也是演员,而且她怀疑自己的已经去世的醉鬼母亲和导演之间有不可告人的往事。接着,安娜的醉鬼母亲出现了,她勾引导演,希望获得些许爱情和柔情。可是在自身的嫉妒、自虐以及厌恶的折磨下,蕾柯尔只是发了一肚子的牢骚。这个时候,亨利克·富勒戈发现十二岁的安娜正坐在沙发上亲眼看着这一切。在母亲离开之后,同一个位子的安娜穿越到了22岁,她和自己母亲一样勾引着导演。而导演拒绝如此,因为他知道他们之间的关系会发展成什么样子,在争吵、谎言和相互谅解之后,安娜离开了剧院。这个时候,教堂的钟声响了起来,但是耳聋的亨利克·富勒戈对这一切无动于衷,他似乎还沉浸在回忆、情人和艺术之中……
应该说,这是一部很有野心的影片,因为在片中,伯格曼把所有的人类都当作演员来对待,他们的一举一动、他们的爱情和情感都是带有目的性的。通过封闭的舞台,伯格曼打开了人类开放的内心世界。而那些演员们,则在爱和恨的栽培下慢慢成长。伯格曼把这种超验体验带入到了电视机的荧幕之中,在排练之外,生活不再是演出,而是一种真实的经历——这种经历,反过来又再一次刺激着演员们,做出对表演或者是对生活的反应。
在片中,安娜所扮演的是斯特林堡话剧《梦》中尹海拉的女儿阿涅斯,而这部影片也借用了《梦》的大量元素。其实,安娜在片中是有所寻觅的,不过她寻觅的并不是手镯,而是记忆和经历。她希望用自己的表演来获取有用的信息和情感,也希望用表演来进一步造梦。而导演和自己的情人、女演员之间的这种寻找记忆或者是寻找情感的片段,也就再一次重新解构了斯特林堡的《梦》。伯格曼对《梦》这出戏剧是钟爱有加,在他的集大成之作《芬妮与亚历山大》之中,《梦》就在结尾闪现——如果抛弃诸多时间和故事上的掣肘,那么我们则可以把《排练之后》看作是《芬妮与亚历山大》的续集——“梦和现实是同一个东西。一切都会到来,一切梦想都是真实。时间和空间混合起来。现实脆弱且总在逃避,想象却在现实虚弱的基础上编制着它的罗网,创造着新的图画和新的命运。”
有人说,《排练之后》是伯格曼对自己的剖析,其实并不是真的如此,伯格曼自己说,他拍摄这部影片完全是想和几个演员以及摄影合作,他希望这部影片能成为他死亡之路上的一个“愉快的插曲”。因为电视播放的限制,伯格曼对影片进行了大量的删节。影片原长1小时12分钟,可是当年电视台播放的版本却只有52分钟。而且,伯格曼原本是想把这部影片拍成喜剧片的,但是经过“无趣”的拍摄过程,这部影片变成了“刻薄的作品”。不过,我们今天依然为能看到这样的影片而高兴——因为不仅是剧中的人物,而是伯格曼预言了作为演员的全人类,都有安排最后结局的自主权。
《魔笛》:伴随一生的咏叹调
《魔笛》本是莫扎特的一出歌剧,也是他所撰写的最后一部歌剧作品。《魔笛》的故事很普通,讲述的是埃及王子塔米诺爱上了夜后的女儿帕米娜,但是帕米娜被坏人萨拉斯特罗掠走。夜后向王子承诺,只要能他能救出自己的女儿,就可以把女儿许配给他。为了帮助他一臂之力,夜后还给了王子一支魔笛。可是,萨拉斯特罗不是什么坏人,他是智慧的主神,也是光明之国的领袖,是夜后的丈夫在临死之前把帕米娜托付给他照顾的。后来,王子识破了夜后的阴谋,打败了她,并最终娶帕米娜为妻。《魔笛》中最著名的,毫无疑问是“夜后咏叹调”。这一段难度极高的咏叹调,堪称是女高音的试金石。
这一出巴洛克风格的歌剧,在伯格曼的手中,却变成了电视电影,被搬到了电视机之上。在这部电影里,伯格曼在莫扎特的音乐和歌词的配合下,做了一出关于戏剧、舞台、故事、梦幻以及现实的游戏。在这场游戏之中,无论是舞台上的演员还是幕后的灯光布景师,甚至是台下的观众,“战壕”里的乐队,都是游戏的一份子。对于在生活中一样接受这个游戏的人来说,这部电影让他们的生活和观念得到了彻底的改善——一次对固有题材和原料的再创造。
伯格曼和《魔笛》这出戏结缘已久,他十二岁的时候,就在瑞典的皇家剧院看到了这出戏,只是当时的演出团体水平有限,这场戏在伯格曼的脑海中留下了冗长而杂乱的印象。后来,伯格曼来到瑞典歌剧院做助理导演,1940年的时候,他作为一个灯光师参加了新版本《魔笛》的演出。而真正让伯格曼对《魔笛》产生难以名状的情感的,则是一所剧院。在某年的十月,伯格曼来到了斯德哥尔摩的一间18世纪的剧院里游玩。剧院的大门并没有上锁,所以伯格曼近距离地参观了这所巴洛克风格的建筑。那是一次令人目眩神迷的经验:独特的舞台设计、清晰的光线质感、宗教般的静谧氛围,使得这里成为了伯格曼心中《魔笛》最好的上演场所。1960年代末期,在瑞典电台音乐部负责人玛格努·安霍宁的提议下,伯格曼开始筹拍电影版的《魔笛》。
电影版的《魔笛》并不是一部简单记录歌剧《魔笛》上演的影片,而是一部根据莫扎特的歌剧重新撰写剧本、筹划拍摄的影片。而且,拍摄《魔笛》的地点并不是歌剧院的舞台,而是另行搭建的摄影棚。在这种情况之下,伯格曼并不要求所有的演员都要扯开嗓门放声歌唱,他所希望的是演员们能用一种温暖、感性、自然的人声来诠释剧中的人物。在寻觅到一整个北欧班底之后,《魔笛》便开始了拍摄。《魔笛》使用了16mm的胶片拍摄,后转制成35mm格式,在新年前夜于瑞典电视台播放。当时的瑞典社会社会对格局的态度并不友好,因为从1968年开始的文化精英之间的论战已经烧到了歌剧方面,而在这个时候大张旗鼓地拍摄一部格局电影,正好受人以把柄。不过,在玛格努·安霍宁的努力下,这部电影还是被拍摄了出来。
站在电影而非歌剧的角度来看,这部影片有很多可取之处。在布景、灯光、镜头衔接之间,充满了伯格曼的特色。更为难等可贵的是,伯格曼在舞台和故事的双重枷锁的限制下,还在影片中加入了很多个人对这出歌剧的理解。影片中,各式各样的隐喻和象征元素层出不穷。看上去,伯格曼真的用有限的素材拍出了一部“童话”。在电影中,所有舞台上的布景和视觉上的景色仿佛都只是顺路经过。突然间舞台上是一个皇宫花园,突然间又变成了白雪皑皑的山峦;霎那间,舞台上是一座监狱,可是转眼之后,监狱消失不见,春天已然到来——应该说,伯格曼用自己的电影,在为所有的乐迷和影迷“造梦”——而他所造的这个梦,在某种程度上分别属于他和莫扎特。
《萨拉邦德》:我可以原谅自己么?
有很多人认为,伯格曼在85岁高龄时拍摄的《萨拉邦德》是他1973年拍摄的《婚姻生活》的续集。其实,这两部电影除了在演员上有关联之外,在内容、情节和气质上毫不相干。片名“萨拉邦德”是一个借用,其原意指的是一种西班牙舞曲。在巴洛克时期,萨拉邦德常常被用在组曲至总。例如巴赫最著名的《无伴奏大提琴组曲》的第三乐章,就使用了萨拉邦德的旋律。萨拉邦德的旋律一般比较舒缓,适合表达较为严肃而缓慢的情感。在片中,卡琳娜一直在弹奏萨拉邦德,成为了一种情感节奏和具有指向性的隐喻。
《萨拉邦德》这部电影,在表面上说的是玛丽安和约翰在分手32年之后的一次会面,但是这部影片真正的主人翁却是约翰的前妻。这个女人留下了一个叫做恩里克的儿子。恩里克是一个音乐家,有一个叫做卡琳娜的正在学习音乐的女儿。恩里克和自己父亲的关系并不好,虽然住得很近,但却很少和父亲来往。恩里克的妻子去世,他便一直没有走出这个阴霾。后来,自己的女儿按照他的意思考上了音乐学院,他却选择了自杀。虽然没有死掉,但是恩里克似乎已经变了一个人。随着玛丽安的到来,恩里克、约翰和卡琳娜这三个人之间开始发生了悄然的变化。了解到这一切的约翰,非常平静。到了影片的最后,约翰来到玛丽安的房间,要求同床而眠。而生活的不幸和悲剧,似乎就在相拥和睡眠中,烟消云散。伴随着萨拉邦德舞曲的节奏,伯格曼罕见的用了一个温情的结尾为自己的影片和自己的职业生涯划上了一个句点。
相比较伯格曼的其他电影,《萨拉邦德》少了一丝锐气和锋芒,多了一丝“一声叹气”式的宽容和淡定。虽然影片的故事并不令人感到温情,但在伯格曼的叙事手法下,它还是给人了一丝温暖和希望。关于女性的遭遇和精神伤害,一直是伯格曼影片的命题,在这部电影中,女性形象,相较他以往电影中的形象,更为健康、更为坚韧也更为坚定。卡琳娜是一个拥有自我意识和自主能力的女性,这和她那个逆来顺受的母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玛丽安则是一个能够倾听和理解的女性,这和他的前夫,那个生活泠漠而自私的男人也形成了比较。或许说,玛丽安的精神层面而非现世处境上,和《呼喊与细语》中的安妮如出一辙——而约翰、恩里克和卡琳娜,则是《呼喊与细语》中艾格尼斯的那几个各有问题的姐妹。
影片拥有一个段落式的结构,每一个段落中间,只有两个人物在互相对话——通过这种封闭的形式,伯格曼依旧表现出了人与人之间的“隔”。虽然拥有温情的结尾,但是《萨拉邦德》带给人的感觉依旧是绝望的,是人们自己把自己送入了“爱情的奥斯维辛”,是人们自己作茧自缚画地为牢,也是亲人互相为对方套上了纸做的枷锁。眼泪也好、细语也罢,为的都是一己私利——人们会畏缩于他人的“恶”,但却会异常开怀地展现出自己的“恶”。虽然约翰在影片最后袒露了自己的肉体和心灵,但这只是暂时的,只是父系话语权向母系话语权的一次短暂的妥协。或许,第二天醒来,改变的还都没变。时年85岁的伯格曼,用这部电影,再一次展示了自己对人性、神性永恒的怀疑。一方面,他释然、平和、追求宁静;而另一方面,他依然对人性之间的隔阂、矛盾和怨恨不依不饶。
=平媒约稿,勿转为感=